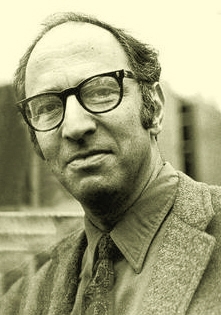 |
人物纪事
一本书问世之后所引发的讨论与思潮,有时会大大超出作者的预期。库恩所著《科学革命的结构》无疑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今年是此书问世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这本书不仅成为从事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者们的必读书目,同时也为社会学、心理学、美学、文学等领域贡献了“范式”、“学术共同体”之类的库恩式术语。科学哲学这等冷门领域能够产生出如此轰动的效应,确实是一个奇迹。
然而对于一本哲学著作而言,越是流行,被误读的可能性也越大。20世纪70年代以来,库恩的思想被其追随者们发展到连他自己也无法辨认的程度。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某些科学社会学家们,主张科学知识不是纯粹自然实在与客观经验的反映,而是由利益、权力等社会因素所建构的,经过宣传、妥协和约定为科学共同体所接受。据说库恩在1980年代的一次演讲中特别批评了SSK(爱丁堡学派发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声称自己的观点跟对方的理解完全是两回事,“我可不是库恩派学者”!
为什么库恩觉得自己被误解了?我们知道库恩理论在描述“哥白尼—伽利略—牛顿”革命时最具说服力。在《科学革命结构》成书之前,库恩写了一本科学史著作:《哥白尼革命》。从这本书里,我们或许能够找到答案。
在记载哥白尼的《天球运行论》诞生以及对外界影响的过程中,库恩确实指出了“哲学和科学思想的大气候”对于产生新的科学观念的重要性,但是他也并未否认学科传统与基础性知识的意义。比如,库恩认为哥白尼之所以断定行星问题具有既简单又精确的解,是因为当时哲学与科学思想的大气候里,有一种新柏拉图主义倾向,“正如哥白尼自己认识到的,日心天文学真正的吸引力是审美方面的而不是实用方面。对于天文学家而言。在哥白尼体系和托勒密体系之间最初的抉择纯属偏好问题,而偏好问题是最难界定和讨论的。”然而,仅凭美感是不够的,“哥白尼是第一个详细地解释地动的各种天文学后果的人。哥白尼与他的先驱们不同之处就在于他的数学工作,也正是部分地因为他的数学工作,一场前人未能发动的革命爆发了。”
另外,哥白尼对托勒密的“革命”也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决绝。“哥白尼和托勒密的决裂仅仅只是在地球的位置和运动方面。他的天文学所植根的宇宙论框架,他的物理学以及他所使用的数学方法,都是在古代和中世纪科学家们建立起来的传统之中。”
随着科学发展,陆续有一些人反思库恩理论。不过,也许库恩与他们的分歧并不大,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是相当投契的。理论物理学家戴森在《想象的未来》一书中写道,“库恩的书很快成为经典之作,然而它却误导了一整个世代的学生以及科学史学者,让他们误以为,所有科学革命都是由观念所引发的。”戴森提出,除了库恩所研究的由观念所驱动的“哥白尼—伽利略—牛顿”革命,还有另一种由工具所驱动的科学革命,比如以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为标志的分子生物学的诞生以及由此而来的一场涉及整个生命科学的革命。
如果对库恩的作品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就会发现,他本人并没有忽视技术在科学革命中的作用。比如哥白尼对托勒密的天文学知识的传承:“哥白尼从《至大论》中得到了许多观测数据和几何方法,以及编制星表的资料。有些问题的处理完全因袭《至大论》。哥白尼甚至比托勒密还接近古希腊的天文学家和哲学家”;“《天球运行论》,除了导论性的第一卷,整本书都非常的数学化,只有精通技术性的天文学家才能读懂”;“哥白尼和他的同代人掌握了比托勒密的数据覆盖面多1300多年的天文数据,因此能够对他们的体系进行精密得多的检测。他们必定更清楚古老方法的内在错误。”
更有趣的是,库恩对于“科学概念的变革”的描述是非常保守和传统的,完全不像SSK那样离经叛道。他认为“科学的基本概念的重大变革都是逐渐发生的……任何个人能够作出的革新范围必定有限,因为每个个人在研究中都必定要使用他在传统的教育中学来的工具,而他穷其一生也不可能把这些工具全部更换。”
实际上,库恩对哥白尼的工作最赞赏的部分,恰恰是技术而非观念。“最重要的是,哥白尼对天际运动的奉献造就了那些无微不至的细节,他靠这些细节探究地球运动的数学结果,并使这些结果适合于已有的关于天体的知识。这一详细的技术性研究是哥白尼真正的贡献。在哥白尼之前和之后都有比他更激进的宇宙论者,他们用粗略的笔触大致勾勒出一个无限的、多世界的宇宙。但他们都没有写出能与《天球运行论》后几卷相媲美的著作,而正是这后几卷首次证明了从运动的地球出发,天文学家的工作能够进行,而且更加和谐,它们为新的天文学传统的开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大师的作品常常会被时代的潮流裹挟,被人们解读出无数原本不属于他自己的思想。我们若想领略真正的妙义,最好还是到原作中去找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