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邝家家庭照,右一为邝文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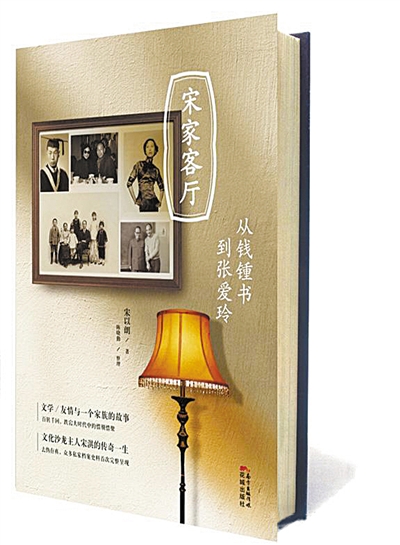 |
| ▲《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书影 |
 |
| 这幅广为流传的张爱玲照片,正是宋家女主人邝文美带她到香港兰心照相馆所拍。 |
■乐享悦读
文学史,似乎是一个“高大上”的东西,大底学者要皓首穷经地写,读者要正襟危坐地读。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是严肃有余,趣味不足。因为读书与工作的原因,自己读了不少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基本上大同小异,先是思潮,再是流派,最后是作品分析。我们感受到的多是作家生活之外的那些“知识”,而关乎作家性情秉性的故事,甚少见到,正可谓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我以为,文学史除了“知识”之外,大底还应该是“有情”的,有“故事”的。宋以朗的《宋家客厅》正是这样一本别样的“文学史”,或者准确地说是主流文学史之外的,“有情”的,有“故事”的文学史现场与片段。
文学沙龙在西方文学中曾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那些沙龙的女主人们风姿绰约,吸引了大批优秀的作家聚集在周围,觥筹交错之余,也畅谈文学,亦或为了吸引沙龙女主人的目光,作家们也是“奋笔疾书”才情四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似乎没有这种文学魅力与荷尔蒙激情并存的文学沙龙,但有温文尔雅、娓娓道来的客厅(虽然沙龙也有客厅的意思啊,但终归是中西有别)。同样的是客厅的主人大多也是女性,著名的如林徽因家的客厅,在那里聚集了不少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才子佳人。
当然,有才子佳人就少不了与男欢女爱有关的“花边新闻”,因此,林徽因与冰心间因为《太太的客厅》闹出了一桩文坛公案。但是,宋淇的客厅里似乎并无这般“风波”,从字里行间可以感到宋琪的客厅里是高朋在座,宾主间品茗论文,和风细雨润物无声;亦有西式派对,佳肴美馔间道尽了人世间的百态千姿与文字中的五味杂陈。广而言之,这“客厅”是泛指中国现代文人的交往方式,既有清谈高论,亦有信札往来,诗词唱和等等文人雅事。
宋淇笔名林以亮,他与张爱玲、钱锺书夫妇、傅雷夫妇,吴兴华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化名流都很熟稔。在宋家的客厅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文化名流的别样面孔;也可见被文学史误读的文人与作品。书中所言甚多,笔者仅举两例。
钱锺书先生的博学与尖锐自不必说,但在《宋家客厅》中,我们却可见钱锺书先生的“人情世故”。钱锺书先生对张爱玲的态度大底上是“必以为然”的。但在接受不同学人采访时,却各有说法。接受安迪采访时对张爱玲评价不高,接受张爱玲研究专家水晶访谈时却说张爱玲“非常好”。
为此,宋淇写信给钱锺书询问为何两个评价差别甚大,钱先生回信答曰:“不过是应酬,那人(指水晶)是捧张爱玲的。”公开的文字与言论,往往难见学人的“真知灼见”,尤其是对他人的评头论足更是唯恐避之不及。但我们在私人的通信中,却可见学人的“真心实意”。我们此前只知道钱先生臧否人物往往“口无遮拦”,在《宋家客厅》我们见到了钱先生的“谨小慎微”与“自如应对”。
对于傅雷先生,我们的印象还是来自于他对年少成名的张爱玲的盛赞与批评,以及《傅雷家书》中的严父形象。在《宋家客厅》中,有一处谈及傅雷曾于1948年于“昆明筹备进出口公司未果”。一向“文艺范儿”的傅雷为何要去开公司呢?从书中看,主要还是因为经济拮据。当年西南联大的学者教授们,也因为生活窘迫而卖文为生,如闻一多先生为人刻印章,梅贻琦夫人拿着女红到菜市场上去卖。无论是闻一多还是梅夫人都是“因地制宜”。而傅雷先生则是“大气魄”,要开进出口公司。看到此处,总是笑出声来。从这里,我们既可见傅雷先生的“恢弘气势”,也可见他的“书生之见”。
张爱玲是宋家的老朋友,也是因为张爱玲与她的作品的关系,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宋淇、邝文美、宋以朗一家。张爱玲在我们主流的文学史中一度被尘封起来。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张爱玲才慢慢地“浮出了历史地表”,甚至有了不少铁杆粉丝——“张迷”,研究张爱玲也成了一门显学——“张学”。
在《宋家客厅》中,宋以朗除了校正了一些张爱玲研究中以讹传讹的史实错误,更多是通过张爱玲与其父宋淇的通信,来展现张爱玲的“私语”一面与更为真切的生存状态。张爱玲作品的基调大多是“苍凉”的,冷酷的,尤其从那本带有自传体性质的《小团圆》中,更可见张爱玲的“冰冷”。但在张爱玲给宋以朗的母亲邝文美女士的信中却显得那般温润动情:“直到你们一转背走了的时候,才突然好像轰然一声天坍了下来一样,脑子里还是很冷静&detached(和超脱),但是喉咙堵住了,眼泪流个不停,事实是自从认识你以来,你的友情是我的生活的core(核心)。我绝对没有那样的妄想,以为还会结交到像你这样的朋友,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再没有这样的人。”或许出于客气,或许出于感激,张爱玲这些“私语”与她在作品中的“叙述”迥然不同。当然,“文如其人”这话也不必完全当真。很可能把作品写得“冷酷到底”的作家,在现实中正是一个“柔情似水”之人。
宋以朗在书中指出好多“张爱玲传”的作者们说张爱玲在美国过得如何清苦寒酸,都是不做调查的“胡思乱想”。他从张爱玲与其父宋淇的通信中,涉及到稿费、金钱的内容,推算出张爱玲当年在美国的生活并不窘迫。
但从他引述的张爱玲与宋淇的一份通信中,我们也可看出,张爱玲在美国的日常生活虽不至于“贫困”,但也不算宽裕,起码日常生活的保障是张爱玲常常担忧的问题,要不她也不至于在给宋淇的信中说道:“我后来再回想离港前情形,已经完全记得清清楚楚,预支全部剧本费用,本来为了救急,谁知窘状会拖到五年之久,目前虽然不等钱用,钱多点总心松一点。如果公司能再拖欠一年,那我对公司非常感谢。”张爱玲到了美国后,为了维持生计,就开始给宋淇所在的电影公司写剧本,为了能专心写作,张爱玲甚至一度从美国到香港居住一年,专门写剧本。除此之外,张爱玲还做翻译,改写自己的旧作等其他差事来维系生存。毫无疑问,这些并不在张爱玲创作之内的“纷扰”,严重地影响了她的写作。
客厅里的“文学史”并非“标准”的文学史,但它的魅力是让我们可以看到作家的“真性情”与多副面孔。主流文学史中的文人作家太过“高大上”了,他们与那些尘封在历史中的作品一样,冰冷地排列在文学史的序列当中。人性本来就是参差百态的,《宋家客厅》这本书就让我们见识到了“冰冷”之外的“火热”,“高大上”之外的“人心世态”。
客厅带有一定的私密性,所谈内容多不易公开,往往涉及隐私。但在《宋家客厅》里却少见与此相关的“花边新闻”,至多有些许的“准风月谈”。这或许就是其格调所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