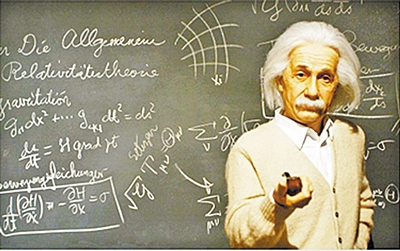 |
100年前岁暮的一天(11月25日),爱因斯坦终于写出了引力场方程的最终形式。
他从1907年发现等效原理到1915年6月,几乎一直在玩儿错误的引力理论,直到7月到10月间才发现旧理论的错误——根据因果律对一般协变性的限制错了,水星近日点的计算错了(差了一倍),引力的拉格朗日量的唯一性证明也错了;不但这些大问题有错,他对张量的基本认识也有错——“幸运”的是,那些错误永远留在他的“8年抗战史”中了,我们才有机会来看辉煌背后的艰辛。在那些年里,他常常表现出犹豫和迟疑:老说他发现了理论的最终形式,几个月后又否定了前面的东西,然后又“自信地”提出一个不同的纲领。(他1915年12月26日给P. 埃伦费斯特写信说,他每年都在抹去前一年写的东西。
直到最后的关头,爱因斯坦还在游移不定。11月7日,他从线性变换的约束中解脱出来(这时才明确坐标系没有实在意义),但保留了幺模变换的约束(这个问题小一些),可11日又倒退了,为度规强加了一个更严格的约束。12日他给希尔伯特写信说那个约束“强化了一般协变性”。
18日,他依然坚持两个约束,却解决了影响广义相对论命运的两个大问题:水星近日点的进动和光线经过太阳的偏折。他很幸运,这两个情形可以用真空度规,他的约束不会带来麻烦,所以错误的理论得到了正确的结果。
25日,我们熟悉的场方程出来了。然而,爱因斯坦到这个时候都不知道张量分析的比安基恒等式,因而不知道他的场方程自然蕴含了守恒律;他还多事地将守恒律作为场方程的一个额外约束。
这段经历令老爱难忘。1933年6月20日,他从德国跑出来,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讲广义相对论的起源说,“在黑暗中探寻我们感觉到却说不出的真理的岁月里,渴望越来越强,信心时来时去,心情焦虑不安,最后终于穿过迷雾看到光明,这一切,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会明白。”
场方程的曲折经历很好反映了爱因斯坦的物理的自信和数学的犹豫,而这似乎一直伴随着他1905年以后的科学生涯。他有时相信纯粹的思维能把握实在,却不相信形式化的论证能作为指引物理学进步的路标。看来,他的纯粹思维主要还是说物理的直觉,如追光和时间盒子一样的思想实验。20世纪30年代,他说他始终欣赏相对论的简单和谐,并不在乎几个“小小的观测预言”。他说广义相对论纯粹是关于自然的一个形式化观点,而不是确定的假设。1917年3月4日,他给F.克莱因写信说,牛顿理论看起来是用势函数完整表达了引力场,但它被度规函数取代了;我毫不怀疑,度规也终有被取代的一天。可是,当老克指出麦克斯韦方程的共形不变性时,老爱说老克高估了“形式化观点”的作用——它们只能作为最终的形式,而不能作为最初的启示。当外尔拿规范场(那会儿还是雏形且有问题)给他看时,他也只关心它的当下的物理基础而看不见它未来的生命。
詹姆斯·格雷克在费曼传记(Genius, the life and science of Richard Feynman)中说,费曼对戴森——1948年去普林斯顿却发现老爱的新论文尽是废话的家伙——说过,爱因斯坦的创造力都来自他的物理直觉,他去玩儿方程(manipulator of eqyations)以后,就停止创造了。最后这个词儿有意思,说爱因斯坦玩儿方程——他对数学的认识,大概也就在解方程的层次。看来,老爱的方法论底线是物理直觉和直觉产生的“自由概念”,他对数学形式的态度总是迟疑甚至保守的。敏锐的物理直觉成就了爱因斯坦,而迟钝的数学感觉影响了他的直觉的发挥。
老爱曾为自己设立了“三个要务(three desiderata)”:统一引力与电磁力,从因果律导出量子论,用连续场论的无奇点解描述基本粒子。遗憾的是,这几个领域都不是仅凭物理直觉能指引的。40岁以后的爱因斯坦逐渐退出了物理学舞台的中央,甚至最后被主流“晾在一边”了。普遍认为是他“失去了早年对物理学真理的非凡直觉”,但我想更大的原因可能是他的数学带不动他的直觉了,借派斯的话说,他“被牵着一步步走进了他自己都不能做出可靠的专业判断的领域”。
他为自己设立了三个基本任务:统一引力与电磁力,从因果律导出量子论,用连续场论的无奇点解描述基本粒子。遗憾的是,这几个领域不是直觉能指引的,甚至已经超出了他的判断能力。
看来,老爱的方法论底线是物理直觉和直觉产生的“自由概念”,他对数学形式的态度总是迟疑甚至保守的。敏锐的物理直觉成就了爱因斯坦,而迟钝的数学感觉影响了他的直觉的发挥。詹姆斯·格雷克(James Gleick)在费曼传记(Genius, the life and science of Richard Feynman)中说,费曼对戴森(Dyson)——1948年去普林斯顿却发现老爱的新论文尽是废话的人——说过,爱因斯坦的创造力都来自他的物理直觉,他去玩儿方程以后,就停止创造了。最后这个词儿有意思,说爱因斯坦玩儿方程——他对数学的认识,大概也就在解方程的层次。
40岁以后的爱因斯坦逐渐退出了物理学舞台的中央,甚至最后被主流“晾在一边”了。普遍认为是他“失去了早年对物理学真理的非凡直觉”,但更大的原因似乎是他的数学带不动他的直觉了,借派斯的话说,他“被牵着一步步走进了他自己都不能做出可靠的专业判断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