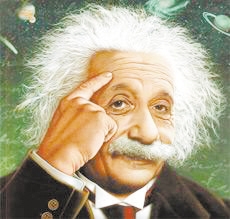 |
■科林碎语
爱因斯坦不是哲学家,却与哲学有很深的渊源。他不像温伯格(Steven Weinberg)那样说哲学对物理学没什么用,也不说哲学是物理学的工具,而是真心同情哲学。他晚年给桑顿(Robert A.Thornton)的信(1944年12月7日)说,他完全赞同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方法的意义和教育价值。可很多人,甚至职业科学家,都缺乏那种眼光,见过千万棵树却从没见过森林。他认为,历史和哲学的背景能帮助我们克服当代人的偏见。是否具备哲学眼光,是区别“匠人”和真正的真理探求者的标志。可是具体说来,爱因斯坦的哲学却不像他的物理那么“纯”。
爱老70岁时总结说,从系统的认识论来看,科学家不过是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当他描述独立于感觉的世界时,他是实在论者;当他认为概念和理论是人类精神的自由发明,而不能从经验逻辑导出时,他是唯心论者;当他认为概念和理论只有为感觉的经验关系提供逻辑表示才算合理时,他是实证论者;当他认为逻辑简单性是研究的不可或缺的有效工具时,他也可以是柏拉图或毕达哥拉斯主义者……这种哲学的“杂糅”,模糊地“涂抹”出一条爱因斯坦哲学演化路线,而这条线恰好平行地引出现代物理学的数学化(特别是几何化)的路线。
多情的哲学家都喜欢将爱老拉入自家的门派——犹如多情的辩证法把一切科学装进自己的竹篮一样。相对论刚出世不久,实证论的祖师爷石里克(Moritz Schlick)就写了一本小册子《当代物理学的空间和时间》,宣扬相对论的哲学意义,特别是实证论的意义。
青年爱因斯坦确乎信过经验论,也自以为是马赫路线的人。他在自述里说,他小时候喜欢“直接与经验接触”,1930年出版的一本《爱因斯坦传》(Albert Einstein, a biographical portrait)说,小爱只想物理实在的问题,不太相信数学的力量,是一个纯粹的经验主义者。大约18岁时,小爱在朋友贝索(Michele Besso)的引介下读了马赫的《力学史》。马赫对牛顿的绝对时空的批判动摇了小爱对“力学作为一切物理学思想的最后基础”的信念,为相对论指引了概念方向。例如,狭义相对论以时空的认识为物理的基础,以“事件”体现实在与感觉的统一。还有它的“操作主义”的时间和长度的测量,都使小爱显得像一个实证论者,所以维也纳圈子的哲学家们欢呼相对论极大推动了“我们时代的哲学”。而广义相对论的等效原理,更是马赫对牛顿水桶实验批判(惯性源于物体的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1913年6月25日爱因斯坦给马赫的信如是说)。
奇怪的是,就在小爱给马赫写信那会儿,老马“变心”了。在《物理光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hysical Optics)的前言(标明时间是1913年7月)里,马赫宣布他不接受相对论,也不承认自己是相对论的先驱——大家知道这一点是在老马去世5年后——《物理光学原理》在1921年出版的时候。1922年,老爱在巴黎与反马赫哲学家梅耶逊(Emile Meyerson)谈话时,说马赫是“优秀的力学家,可悲的哲学家”。
马赫没说为什么“变心”,他答应在“续篇”里细说,但我们没看到下文。老马大概是发现了小爱的“背叛”。原来,小爱所说的“感觉”根本不是老马的“感觉”。小爱说的经验,如光速不变和等效原理,以及更早的永动机、热分子运动等,都不是直接的感觉的“基元”,而是“所有物理经验的综合”。在“真”马赫主义者看来,它们不是感觉的经验,而是近乎“假定”的东西。
小爱的“反心”其实早就萌芽了。在1901年,小爱告诉格罗斯曼(Marcel Grossmann,帮助他完成广义相对论数学的朋友),认识复杂现象的统一真是奇妙的感觉;而对直接的感觉经验来说,那些现象是相互分离的。小爱从经验感觉来的是“统一”,是概念,那是他的感觉方式,所以不觉得有“假定”的成分。他却不知这已经超出了马赫的“底线”。
老爱晚年回忆,他对马赫哲学的态度转变大约就发生在1900年后不久——也许就是他给格罗斯曼写信那个时期。他发现,他对从已知事实来构建理论的方法感到失望了,而且越来越失望;最后终于明白,只有发现了普适的形式原理才可能得到确定的结果。
小爱似乎只是在“操作”意义上借了马赫的感觉经验,他骨子里想的还是康德的先验概念。经验对他只是一个与物理实验相关的“借口”,最终他还是“皈依”了形而上学:1930年11月28日,他给石里克写信说,你的表述没有代表我的概念,你太实证了……我坦白告诉你,物理学是从概念去构造现实世界的模型及其法则结构……“你会惊讶‘形而上学家’的爱因斯坦,但每个四脚和两脚的动物在这个意义上本来就是形而上学家。”
1933年,老爱在牛津大学演讲《理论物理学的方法》时,终于道出了他自己的“经验论”:我们的经验令我们相信,自然是最简单的可能数学思想的实现。而演讲开头的一句话更有意思:对科学发现者来说,想象的产物是那么自然而然,所以不该认为是思想的创造,而应看作本来的实在。在一定意义上,“我相信纯粹的思想能把握实在。”在老爱看来,想象约等于实在——这不仅把经验推得更远,也把自然拉得更近。这当然是康德的“为自然立法”的传统。
不过,老爱对康德的“先验”概念也有过动摇。1918年夏他给玻恩(Max Born)写信谈读《形而上学导论》的感想,认为“必须把这个‘先验的’冲淡为‘约定的’”。几十年后,玻恩在通信集里批注说,那会儿爱兄更喜欢休谟,是个十足的经验论者。不过从其他文献看,老爱似乎从来没有“失足于”经验论,顶多是河边湿脚而已。“约定论”是大数学家彭加勒的概念。1921年,爱老师在普鲁士科学院报告《几何学和经验》(Geometrie und Erfahrung)时明确表态:“从永恒的观点看,彭加勒是正确的”。可是一年之后,在同法国哲学家们讨论他与康德哲学的关系时,老爱却“没有立场了”:“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康德,任意发明的概念对构建科学是必须的——至于是先验的还是约定的,我无话可说。”
我们从爱老师在不同时空的言论,可以看到他在哲学上的“摇摆”。但不管怎么摆,最后都落向一个“基点”:概念是自由发明的,不是从经验得来的。物理学从这个起点出发走进了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