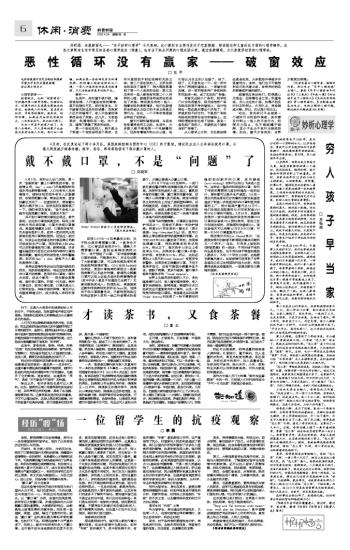
 |
我的母亲生于1900年,是长沙近郊一个货郎的女儿;10岁丧母后,靠我外公早出晚归四处叫卖养家糊口,她还要照看年幼的妹妹,承担全部家务活。真可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16岁那年,母亲与我父亲结为夫妻,她是苏家娶回的第一个媳妇,因品性纯良、聪明伶俐、能干勤俭而深得苏家上下的喜爱。其时,苏家由我年仅18岁的三伯父主持家政。三伯情商高,有智慧,处事公平,懂得设身处地替他人着想,把整个苏家治理得一派和睦景象。三伯母和我母亲的关系极好,在她的推荐下,母亲被指定为内当家,协助三伯父管理全家事务。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母亲的形象特别高大,绝对是个英雄。四次长沙大会战,我的家乡四次遭受日寇的烧杀掳掠。但是,在母亲的脸上,从来看不到愁苦的神情,无论家里遭受多大的劫难,她总是保持乐观的姿态,面对困难从不放弃努力。战乱中的最大风险,不是财产损失,而是生死威胁。在我的记忆中,母亲至少经历了两次极为惊险的生死考验。
第一次是在1941年冬,日寇第三次进犯长沙,我们全家被迫再次逃难至廖家冲,当时那儿是一片封闭的山丘和茂密的树林。逃难途中,我们不幸遭遇一队日军,一阵机枪子弹扫过来,我们一家人被冲散了,母亲带着两个弟弟,奔逃在山间的小路上。母亲是小脚,走不快,两个弟弟年纪幼小,如何跑得过日军!眼看日军就要追上来了,母亲急中生智,双手搂着两个儿子,倒向山坡草丛中,并顺势滚下山坡,躲过了一劫。全家人聚首后,母亲讲述这件事时,表情平静,语气从容,丝毫没有惊魂未定的样子。
第二次是在1943年初冬,我家刚逃难回家不久。一天,我二哥出门办事,到半夜还不见回来,全家人都慌了,到处寻找;一连找了三天,也未见踪影,不免万分焦急,生怕出了意外。那个年代,家里没了个人,司空见惯,每个人都像狂风中的一片树叶,不知什么时候就掉下来了。“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也只有经历过战乱的人才会有这样切肤的体会。
第三天傍晚,总算有了二哥的消息,东山镇的一个亲戚送来口信:二哥被“忠义军”抓去了,现被关在他们的队部。“忠义军”是个什么组织,我们这些老百姓根本搞不清楚,只知道他们是“国军”部队。当时,长沙一带有各式各样的“国军”队伍,胡乱抓人的现象也很普遍,且往往以抓“日军间谍”名义去领取奖赏。在利益的驱动下,他们就不惜以无辜者的人头换大洋。
“忠义军”带给我家的话是,没把我二哥按“间谍”处置,但要求拿一百块光洋去赎人。经过几次逃难后,我家家底已败落得差不多了,全家拼尽气力,才勉强凑了30块大洋。对方开价100大洋,只拿30块去赎人,大家不免担心,万一激怒了“忠义军”,不仅二哥赎不回来,去的人可能也要搭进去。
三伯决定亲自去赎人,母亲坚决不同意,说:“你是当家人,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苏家的天就塌了!还是我去吧。我一个女人家,他们能把我怎么样?”起初三伯不肯让她去冒险,但母亲坚持要去,态度十分坚决,三伯只好同意了。
母亲是小脚,走不了远路,就由一个亲戚与四哥、五哥用滑竿轮流抬着她去,且都打扮成轿夫模样,身上穿得破破烂烂,万一出了意外,不至于又被拿去当了人质。到了东山镇,母亲走进“忠义军”队部,看见二哥安然无恙,总算放了一大半心。当晚,母亲在镇上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宴请“忠义军”的全体成员连官带兵一共才6人。母亲管家多年,是见过世面的,宴会上表现得落落大方,让店家好酒好菜只管上,“忠义军”的人吃喝得很开心。期间,亲戚按事先跟母亲商量好的,溜到“忠义军”队部,将二哥放出来,让他借着夜色逃跑了。
宴毕,母亲爽快答应拿钱赎人,再到“忠义军”队部,一看二哥人不见了,她马上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找“忠义军”要人。母亲的表演很逼真,对方没看出破绽,就猜测说,人大概是自己跑了,没准已经到家了,跟放走也没什么两样。母亲听他们的口气,好像还是想要赎金,索性一闹到底,让亲戚出面,请当地几位有头有脸的绅士来“讲理”。几经调解,最后商定,由我家亲戚和那几个绅士一起出10个大洋给“忠义军”,了结此案。而事实上,这10个大洋是我母亲事先交给亲戚的,他们只是出力、出面子,并没有真的出钱。
这件事过去快80年了,我每每忆起,仍对母亲当年的机智和胆略钦佩不已!
(作者为长沙市退休耄耋老人,探过矿,教过书,经过商,著有《活好》《活明白》《筑梦人生》等书)

 下一版
下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