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37年后,本文作者与北戴河会议期间的室友、著名气象科普作家林之光先生(右,现年83岁)在国家图书馆忆往留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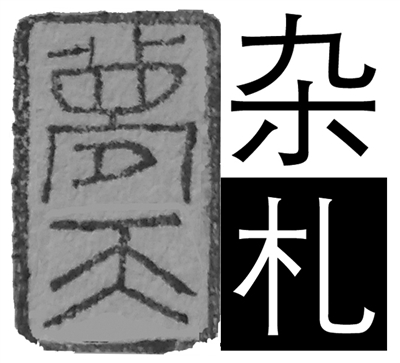 |
□ 卞毓麟
纪念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成立40周年
编者按:2019年是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成立40周年。日前,旨在回顾、总结科普创作事业与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发展历程,展示我国科普创作新成就、新变化,以及广大科普作家积极向上的创新和奉献精神的主题征文活动已经启动,今起本报陆续刊出相关文章,敬请读者朋友垂注。
1981年10月1日,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后更名中国科普研究所,简称“科普所”)启用大印,正式开张。科普所当时与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后更名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简称“科普作协”)合署办公,“一套人马,两块牌子”,高士其任名誉所长,中国科协普及部部长黄汉炎兼任领导小组组长,梅光(第一任所党委书记)、王麦林和章道义为领导小组组员。他们协力带领为数不多的人马,克服种种困难,在不长的时间内完成许多重要的工作,令人钦佩。
其中的一项工作,就是1982年4月下旬在北戴河召开科普创作的理论研究及重点创作选题计划会议。从生活节奏已大大加快的今天来看,此会开了一个星期,用时似乎“奢侈”;但当时能聚集那么多志同道合的战友,历时一周悉心研讨,这本身就是成功。
这次会议由梅光和章道义总负责,与会者分成4组,作为一种历史记忆,值得罗列名单如下:
第一组(14人) 徐克明、王梓坤、谈祥柏、夏树芳、张三慧、凌永乐、王真、卞毓麟、林之光、费金深、高庄、孔德庸、向华明、郭正谊。
第二组(15人) 史超礼、凌肇元、蔡幼伯、程鸣之、朱先立、王健、刘寿听、冯永亨、佟屏亚、朱毅麟、林仁华、王明慧、王洪、袁清林、汤寿根。
第三组(17人) 周孟璞、符其珣、郑公盾、金涛、赵之、黄连城、陈渊、周稼骏、文有仁、梁烈、李元、吴伯泽、何寄梅、王惠林、蔡伟蓉、陶世龙、黎先耀。
第四组(12人) 王国忠、司有和、朱志尧(缺席)、刘后一、张锋、郑延慧、陈天昌、盛如梅、孔述庆、陈日朋、孔小梅、郭以实。
我统计了与会者的年龄分布:40岁以下10人,41~50岁18人,51~60岁30人,60岁以上5人,我本人39岁。2002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章道义主编的《中国科普名家名作》,上述大部分与会者的简况均可在书中查到。
最后一天的全体会议上,有14人发言交流经验,可谓精彩纷呈。如王梓坤介绍创作《科学发现纵横谈》的动机和艰苦过程;谈祥柏介绍多年来研究马丁·加德纳的经历;林仁华介绍《军事科普丛书》受到全军指战员的欢迎,以及全体作者和编者受到总政治部嘉奖的喜讯……大家深感受益匪浅。
在会上,科普所决定出版内部参考资料《评论与研究》,第1期当年6月就面世了,水准可嘉。我所见到的最后一期《评论与研究》是1986年12月出版的第10期,刊末仍有“征稿简则”,但我不知它一直出到何年何时。
参加这次北戴河会议,对我很有帮助。在全体与会者中,当时我最熟悉的是李元和吴伯泽。李元长我18岁,与我是天文同行,亦师亦友。吴伯泽长我10岁,是科学出版社的才子,我们都钟情于引进外国科普名著,同时我也是他所在的编译室的一名主要译者——翻译阿西莫夫著作,并年年参译《美国科学年鉴》。
不少久闻其名的科普人物,都在这次会上见到了,令我分外高兴。尤其值得回忆的是,我在中学时代,读苏联别莱利曼教授《趣味物理学》《趣味力学》《趣味天文学》《趣味几何学》等名著简直着了迷,其中好几部书的译者就是符其珣先生。我很佩服他的译笔,也佩服他的严谨和勤奋,还有《少年电机工程师》、伊林的《自动工厂》等也都是符老翻译的。符老出生于1918年,长我25岁,在北戴河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和蔼,谦逊,开朗,坦诚,机智,幽默……会间观光,他还在路旁掏钱骑马照相。1987年,我突然获悉符老去世,顿觉悲伤莫名。
我在北戴河会议上的大会发言,题为《我为什么要研究阿西莫夫》。会后,经《评论与研究》约稿,此文在该刊第1期上刊出。我谈到,研究阿西莫夫的根本目的,简而言之还是“洋为中用”:一是直接以此向读者普及科学知识,二是供国内作者研究与借鉴。文中写道:
1979年,我与友人黄群合作翻译阿西莫夫著的《洞察宇宙的眼睛——望远镜的历史》。我们都深深地被这本书中优美的科学内容与隽永的文字风格打动了……于是,在翻译阿氏作品的过程中,对他的研究也自然而然地开始了。
在会上,大家对研究课题提出了不少很好的想法。例如:
我国现代科学小品研究(黎先耀)
近年来科学诗歌创作的进展及其特色(张锋)
少儿科普与美的教育(郑延慧)
竺可桢与科学普及(高庄)
戴文赛等天文学家的科普活动与我国天文学的发展(李元)
贾祖璋作品研究(陈天昌)
别莱利曼及其作品研究(符其珣)
马丁·加德纳及其数学科普作品研究(谈祥柏)
阿西莫夫科普作品研究(卞毓麟)
……
在北戴河会议之前,我研读阿西莫夫已有多年。1981年5月,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了黄伊主编的文集《论科学幻想小说》。此书初步编完时,黄伊意识到阿西莫夫“缺席”实为一大遗憾。遂经郑文光推荐来函约稿,意谓请撰一篇《阿西莫夫和他的科学幻想小说》,字数少则数千,多可逾万,要求言之有物,交稿时间以一星期为限,过时不候。我对“过时不候”印象深刻,心想这是您找我“救急”,措辞何以如此生硬?但看在阿西莫夫面上,仍全力以赴写出13000字的长文,一周之后准时交卷,黄伊殊觉中意。此后,我研究阿西莫夫,主要是专注于他的科普作品。
在北戴河会议上,我还提到阿西莫夫的科普创作动机。当时,汤寿根正主持中国科普作协主办的双月刊《科普创作》,随即就此向我约稿。未久,我与阮芳赋合作的《阿西莫夫的科普创作动机及其他》一文即在《科普创作》1982年第4期上刊出。
也就在1982年,我加入了中国科普作协,有了更多的机会向前辈学习,与志趣相投的同道切磋,在科普创作之途上迈出了新的一步。今逢科普作协40华诞,这篇“小忆”,正好兼志庆贺。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前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客座研究员,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名誉理事长)

 下一版
下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