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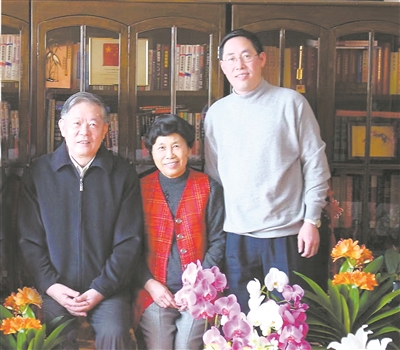 |
| 吴岳良(右一)与周光召夫妇的合影。吴岳良供图 |
◎吴岳良
编者按 8月17日,“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周光召因病在京逝世,享年95岁。周光召先生毕生从事高能物理和核应用理论研究,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和战略核武器的设计、研制和试验方面卓有成就,是国际公认的杰出理论物理学家。本报邀请周光召先生的学生和同事,追忆他胸怀祖国、服务人民,追求真理、敢为人先的精神风范。
获悉周光召老师于2024年8月17日永远离开了我们的消息,我几乎不敢相信,心情久久不能平复。自己仿佛还沉浸在今年5月15日,为老师庆贺他从事科学事业70周年暨95华诞的情景中。那天,我们在他工作过多年的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举办了“周光召先生学术思想和科学精神研讨会”。
回想起40多年来从老师那里得到的精心培育和持续鼓励,以及他的学术思想、科学精神和家国情怀对我的熏陶,感慨万分,脑海里总是浮现出他的音容笑貌以及与他探讨和研究科学前沿的画面。
“既要向同行专家学习,又不要轻易相信权威”
记得我第一次听到周光召这个名字还是在南京大学求学期间。老师们在谈及我国理论物理学界最为敬佩的中青年理论物理学家时,都曾不约而同地提到周光召。周光召作为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先生的得意弟子,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他在基本粒子物理领域就作出了具有国际影响的杰出成就,包括在国际上首次引入相对论螺旋散射振幅概念和相应的数学描述,建立起螺旋度的协变描述和极化粒子反应的相对论理论。而他简明扼要并解析地推导出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PCAC),更是对弱相互作用理论起到了重大推进作用。他也因此被国际粒子物理学界公认为是PCAC的奠基人之一。此外,他还较早注意到K介子和π介子之间的对称关系等。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的4年里(1957年2月—1961年2月),他发表了30余篇论文,引起了国际同行的高度关注,成为蜚声国际科学界的青年理论物理学家。
周老师能在短短4年时间内做出如此多的原创性成果,一方面得益于他在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习期间打下的坚实数理基础,并从导师彭桓武先生那里领悟到了科学思维的方式和科学研究的方法;另一方面得益于他勇于思考、善于分析、敢于挑战、不迷信权威,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
周老师曾给我讲过他初到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的一段难忘经历,一直让我记忆犹新。1957年春,年仅28岁的他被国家选派到该研究所从事基本粒子物理的研究工作。杜布纳是位于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小镇。当时有来自苏联、中国、越南、朝鲜等国家的粒子物理和核物理学家一起开展粒子物理前沿研究。
周老师刚到杜布纳不久,在一次由各国物理学家参加的学术讨论会上,一位苏联教授在会上报告了对粒子自旋问题的研究成果。周老师认为这位教授的观点明显不对,就站起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而那位教授却用不以为然的目光看了他一眼,很不高兴地说:“你的观点没有道理!”面对权威专家的这种回答,周老师并没有直接反驳。会后,他默默地研究了3个月,一步一步地证明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并先后把研究成果写成《极化粒子反应的相对论性理论》和《静质量为零的极化粒子的反应》两篇论文,发表在苏联的《实验与理论物理》杂志上。这两篇论文成为在散射理论中最先给出粒子螺旋度的相对论性协变描述。从此以后,这位教授不得不对这位来自中国的年轻科学家另眼看待。讲完这个例子,周老师深有感触地对我说:“要让别人瞧得起自己,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做出比别人更突出的研究工作。既要向比自己强的同行专家学习,又不要轻易相信权威,要有自信。”他的这番经历和教导,一直激励着我之后的科研工作。
1961年,周老师刚从苏联回国就正式加入核武器研制队伍,协助邓稼先完成核武器理论设计工作。这期间,他仔细检查了原子弹理论设计过程中的“九次计算”,最后巧用“最大功”原理反证了苏联数据有误,结束了原子弹设计过程中近一年的争论,为原子弹的研制成功作出了突破性贡献。
周老师隐姓埋名近20年,后被调到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在不到8年的时间里,他只争朝夕,在很短时间内迅速站到理论物理研究的前沿,再次做出了一系列有重要学术意义的科研成果,包括指导和带领国内一批中青年理论物理学家在相互作用的统一、时空对称性破坏、非线性σ模型、量子场论的大范围拓扑性质及其与量子反常的联系等方面做出许多独创性工作。在统计物理和凝聚态物理方面,他与合作者一起系统地发展了非平衡态统计的闭路格林函数方法,并应用到激光、等离子体、临界力学、随机淬火系统等领域。他所取得的一系列科研成果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重视。
取得这些科研成果和周老师与自然对话的科学思维方式分不开。在跟随老师5年的博士学习生涯中,他常常对我说,理论物理研究是去探索和发现自然界的基本规律,而不是去创造规律。因此,我们要从整个自然界(从极小粒子到极大宇宙)本身可能的运动和演化规律来思考和探讨。在与老师的研讨中,不难发现,他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与自然对话式的和联想式的创造性思维方式,是一种从第一性原理思考和求解问题的思维方式。这样的思维方式不受局限、不易固化。老师总是坚信,任何复杂现象背后一定会有一个更简约的规律在支配。这也是为什么跟他合作和共事过的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他总是会很快抓住问题的要点,并能做到化繁为简,使得遇到的问题迎刃而解。
“时刻准备接受祖国交给的任务”
周老师非常热爱理论物理研究。在他看来,理论物理是研究宇宙、物质、能量、时间和空间以及其相互作用和运动演化所遵循的最基本规律的一门学科,也是最具基础性、前沿性、交叉性和综合性的一门学科。理论物理研究需基于大量物理现象和物理实验,依据简单的物理原理和物理图像,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辩证思维,利用严格的数学公式和数学方法,高度概括和演绎归纳出具有更普遍意义和深刻本质的基本理论。
一个成功的理论不仅能成为描述和解释自然界已知的各种物理现象和运动规律的理论基础,而且还将是预言和发现自然界未知的物理现象和基本规律的理论依据。科学史表明,一旦基础理论研究获得根本性突破,必将导致科学革命,并促进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创新,引发变革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的涌现,触发相应的工业革命。
即便如此,面对国家需要,周老师曾放弃他热爱的理论物理研究。
老师所处的那个年代,可谓是粒子物理发展的黄金时代。他在杜布纳的研究工作处于粒子物理研究的最前沿。他的研究成果与同时代做相关研究工作而后来以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物理学家处在同一水平。
杨振宁先生评价:“周光召在杜布纳工作时期是多产的。他在苏联《实验与理论物理》杂志上发表了很多文章。当时我在美国研究了他的这些论文,尤其是他关于赝矢量流部分守恒的工作。他在美国被认为是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最杰出的年轻科学家。”李政道先生也曾这样评价道:“周光召是世界著名理论物理学家。20世纪70年代在和他见面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了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许多重要工作。他的工作得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评价。另外他的文章通常都写得深入和简洁。”周光召的合作导师马尔可夫说:“周光召同志在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室工作期间完成了一系列研究工作……他是一位特别有能力且有前景的科研人员……”
然而就在周老师的研究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并可能获得重大突破时,国际环境变化,苏联撤回对华技术援助,使得中国原子弹研制面临巨大困难,急需相关人才。为此,他主动请缨,决定立即回国。由他负责起草给第二机械工业部领导的联名信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作为新中国培养的一代科学家,我们时刻准备放弃我们的基础研究,接受祖国交给的任务。我们深信,中国一定能够造出自己的原子弹。”
当时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所长布洛欣采夫给钱三强写信要求延长周光召在杜布纳的访问时间。他在信中写道:“特别关注年轻的科学家周光召,他已经独立完成了大量的理论研究。按照波戈留波夫教授的建议,周光召至少还应该延期1年,这样可以丰富他自己的研究,对研究所也是很有益的。”
然而,周老师谢绝了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的挽留,于1961年2月回到祖国,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九院理论部第一副主任。他与彭桓武、邓稼先等一批科学家一起,进入中国原子弹研究核心部门,开始了近20年隐姓埋名的奋斗历程。直到20世纪80年代,周老师才回归了他热爱的理论物理研究事业。
“真理的获得只有通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才能达到”
1980年9月,周老师应邀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和加州大学任客座教授,受到美国物理学界的热烈欢迎。他被国外同行视为中国理论物理学界的代表人物。时任美国物理学会主席马夏克教授为欢迎周老师的访问,专门为他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举行了以弱相互作用为题的学术研讨会。许多国际知名物理学家包括多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参加了会议。1981年9月,周老师又受邀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访问。正当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学术生涯时,一个重大的人生转折又出现在他的面前。他被急召回国参加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选为中央委员。
为推荐周老师担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彭桓武先生在写给卢嘉锡院长和胡克实副院长的信中这样评价他:“周光召同志是我的研究生,后又长期和我一道进行核武器的理论研究。他具有优秀的学习成绩,经过国际竞争性的基础科研锻炼,也经过迫切性的国防科研锻炼,能体会和处理理论与实验、科研与实用的结合问题。除工作富有创造性和学风严谨外,他还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一定的行政领导和对外竞争、联系的经验。所以,为进一步发展我所的工作,我现在正式建议由周光召同志担任我所所长,并免去我的兼所长职务。”
在彭桓武先生的力荐下,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1984年4月开始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87年1月,周老师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
在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期间,周老师努力倡导和营造一种清新的学术生态环境,奉行开拓精神,在中国科学院形成民主、团结、融洽、活泼的学术气氛,决不允许用行政手段干涉学术自由,为科学家们创造了一个身心舒畅的工作环境。他认为“科学研究中不存在先验的‘框框’”“真理的获得只有通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才能达到”。他倡导的这些理念使中国科学院形成了浓厚的学术气氛,为出成果、出人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也是他亲身参与和领导“两弹一星”并取得巨大成功所总结和归纳出来的宝贵经验。
面对当时的国情和院情,为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他在中国科学院提出新的办院方针:把主要力量动员和组织到国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同时保持一支精干力量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创新,并提出了“一院两制”的办院模式。此外他实施了一系列新的举措,包括推动建立联合实验室、联合研究中心、科技促进经济发展基金会、科技园区,发展高技术产业,进行产学研联合开发等,并倡导有条件的研究所创办高新技术企业,改革完善管理机制,使中国科学院在改革中进一步蓬勃发展。在今天看来,这些都是在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变化步入特定历史时期,为顺应时代前进的步伐,对国家最高学术机构进行的一次重大变革。
另一方面,为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周老师推动实行国家科学基金制,并推进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开放;在体制机制和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提倡开放、流动、联合、竞争,实施研究所分类定位,建立了青年基金、所长择优基金、博士后制度、职称特批制度,以及香山科学会议研讨模式等。
与此同时,周老师集中精力培养人才,着力解决中国科学院科研队伍的“代际转移”问题。他特别爱惜年轻人才,每当看到年轻人的科研取得重大进展和突破时,他都会特别关注,有时还会专门请他们做成果介绍,甚至亲临实验现场进行考察,给予青年人才及时的鼓励和支持。
“要努力做时代需要的事情”
在中国科学院经过多年改革,逐步迈入稳定发展的新阶段时,周老师开始思考提拔年轻人来担任中国科学院的领导职务。
1995年,我回北京参加第17届国际轻子—光子会议。该会议是在我国首次举办的国际高能物理领域最大规模的一次会议,周老师担任大会主席。会议期间,我给周老师汇报了我的一些科研进展,并探讨了粒子物理的未来发展和我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他向我透露了他的一个愿望,希望从领导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继续开展粒子物理的前沿研究,让年轻同志来担当领导重任。得知老师的这个愿望,我当即表示,将全职回国与老师一起进行研究。这之后,我保持与老师更多的联系,对粒子物理理论前沿方向进行深入探讨,很快构建了一类大统一模型(电弱强三种相互作用力的统一),并对粒子物理标准模型中十多个参数给出与实验相自洽的预言。
1996年,我全职回国,与老师一起瞄准粒子物理理论的理想目标,对所有相互作用力的统一理论开展研究。记得有一天,我们讨论中遇到了一个疑难问题,没想到第二天一早还不到7点就接到老师的电话,他说找到了解决方法。我既兴奋又担心,老师这么大年纪,还在不停地思考,想必他一夜都没有睡好。有时我们讨论问题会忘记时间,直到师母催促才会想起还没吃饭。我们持续研究了大半年时间,把初步研究结果整理后,在《中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对所有基本力的一种可能的统一模型》的论文。
1997年,当我们的研究告一段落后,老师对我说,他又不能继续再做理论物理研究了,统一理论这个目标和愿望希望我能继续思考和研究。我知道,他已当选为中国科协主席,并领衔担任973计划顾问组组长,必须面向国家的需要和社会的期望,发挥他在那个岗位上应有的作用。
自20世纪20年代爱因斯坦提出统一场论思想以来,无数理论物理学家为建立统一理论而不断探索。为了不辜负老师的期望,实现能描述从极小粒子到极大宇宙的统一理论,我从没停下探索的步伐,沿着与老师起初研究的思路,经过不断地从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再肯定这样循环往复的思考探索,直到2018年基于新的引力量子场论框架建立起理论上自洽的超统一场论。当得知老师希望了解超统一场论的进展时,我专门去医院给他详细汇报了这个理论的建立过程和引入的相关新概念。尽管不知老师究竟听清楚了多少,但见他不时地用眼睛看着我,有时露出会意的微笑,其中的一只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我再次被老师感动,心里默默地想着,能给予老师最大的安慰就是在理论物理前沿研究中不断取得突破,在世界科学史上留下中国科学家浓墨重彩的一笔。
周老师热爱科研,但他更爱祖国。
他曾说,时代决定选择的大方向,要努力做时代需要的事情。周老师以他高尚的爱国情操、包容的人格魅力、渊博的学术造诣、严谨的科学作风、长远的战略眼光作出了无愧于时代的杰出贡献,赢得了国内外的高度评价,成为功勋卓著的一代科学巨匠和学界楷模。他的学术思想、科学精神和家国情怀将世代相传、永续千秋。
惟楚有才光召,智韬略惠乾坤,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学术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