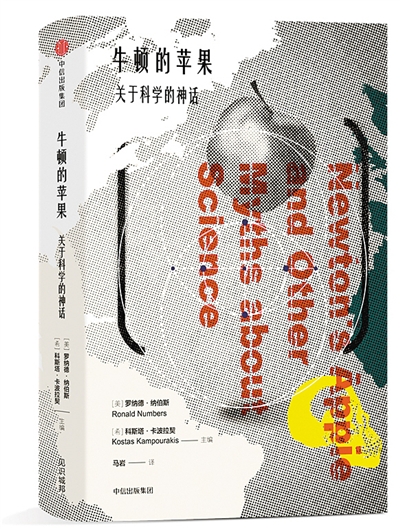 |
| 作者:[美]罗纳德·纳伯斯 [希]科斯塔·卡波拉契 译者:马岩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 出版时间:2017年12月 |
字里行间
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里用略带血腥的墨水描绘了这样一幕:亚历山大女数学家希帕蒂亚被“一群蛮人与残忍的狂热分子们”用尖锐的蚌壳“将她的肉从骨上刮下,把还在颤抖的断肢投入火中”。发生在公元415年的这一幕似乎标志着宗教迫害科学的开始,而1000多年后惨遭火刑的布鲁诺更是“科学的英雄的殉道者”的代表。
两个事件为黑暗的中世纪树立了界碑。但这不是历史,而是“神话”。希帕蒂亚的死是因为政治,布鲁诺的死是因为异端的神学,与他支持日心说无关,其实哥白尼也想着让人“从万物中看出造物主确实是真美善之源”(《天体运行论》导言)。这样的神话在科学史上很多,于是罗纳德·纳伯斯和科斯塔·卡波拉契编了两本书来揭露它们,前编叫《伽利略的囹圄》,续编叫《牛顿的苹果》,副题是“关于科学的神话”——这里的神话(myth),没有特别的含义,与其说是“错话”或“谎言”,不如直呼它“迷失”。
科学和科学史的迷失,大约因为道路分岔了:宗教的偏见、历史的误会和方法的错爱。选向不同,故事就走样,且越走越远。我们熟悉的一些“课本常识”,如开头说的中世纪的黑暗,又如哥伦布证明地球是圆的、哥白尼把人类赶出宇宙中心、伽利略为哥白尼身陷囹圄、达尔文颠覆自然神学……都是后人的误会或歪曲。伏尔泰说认识中世纪就是为了蔑视它,而我们大约是因为不认识它而无视它的存在,当然更不知道中世纪的科学和宗教。
说中世纪是科学的真空,多半是为了更好地说文艺复兴的革命。有趣的是,那“复兴”的古希腊罗马文明,却流落在罗马帝国衰亡后的东方,藏在中世纪的“黑暗”里。走进中世纪,我们会看到它流行的“自由七艺”——语法、修辞、逻辑、几何、算术、音乐和天文学。“七艺”中博学的部分被引向科学,其神圣性则被引向宗教,宗教与科学一直“共生”着,众多学科处于萌芽状态,与宗教的勾连剪不断理还乱。到了19世纪,才有人大张旗鼓地挑起科学与宗教的战争。“论战派”的观点是,基督教的兴起是科学衰落的原因,如古典历史学家Charles Freeman有本书叫《西方思想的关闭:信仰的兴起与理性的衰落》,书名令我想起近些年的物理学派斗争。斯莫林为批判超弦理论写了一本《物理学的困惑》,其纲领性副标题与Freeman是同一思路:“弦理论的崛起与科学的衰落”。物理学家戴维斯也说,物理学的时尚变了,变得像宗教,“拿信仰做基础”。但信仰不等于宗教,更多时候它只是像爱因斯坦说的“宇宙宗教感情”。很多论战都发生在不同信仰者之间,而不是宗教与科学之间。
从宗教影子里跑出来,会看到更多的神话,如牛顿的苹果,伽利略的比萨斜塔实验,达尔文与华莱士的进化论……它们最终都可归到信仰。更有代表性的例子可能是狭义相对论与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神话——那实验与相对论的创立没多大关系,很多课本却爱从它说起引出相对论。课本走的是从实验到理论的传统路线,大多数学科一直走在这条路线上。但爱因斯坦是从麦克斯韦方程的协变性切入的,相对论可以基于两个假定逻辑推演出来,那么任何实验都将是它预言的结果而不是它生成的基础。这就是另一条路线了。一个人选什么路线,不是问题决定的,而是他的“宇宙宗教”信仰决定的。没有这种信仰和感情,科学真的会“迷失”。
作者在乱纷纷功利的科学生态里重温一些老掉牙的、谁也不在乎的问题,是因为那些神话的“谬种”流传太广了,总妨害我们认识科学是什么,应该怎么做。借一句老话说,我们的有些麻烦不在于无知,而在于知道了太多不是那么回事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