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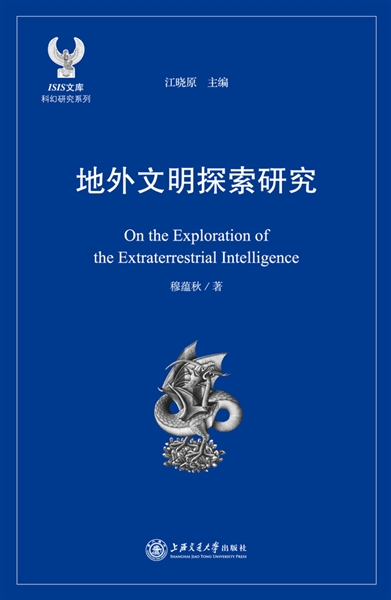 |
| 《地外文明探索研究》,穆蕴秋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 |
大约从2004年开始,我尝试耕种一小块“学术自留地”———后来我给它定名为“对科幻的科学史研究”。穆蕴秋的论文《科学与幻想:天文学历史上的地外文明探索研究》是这个方向上的第一篇博士学位论文。
最初我耕种这块小自留地,只是因为积习难改,什么事情都想和“学术”联系起来,看科幻电影和科幻小说也不例外。后来搞得比较认真了,就开始思考一些相关的理论问题。
一方面,在我们以往习惯的观念中,科幻作品经常和“儿童文学”“青少年读物”联系在一起。例如,就连刘慈欣为亚洲人赢得了首个雨果奖的作品《三体》,它的英文版发布会居然是在上海一个童书展上举行的。这使得科幻作品根本不可能进入传统的科学史研究范畴之内。科学史研究者虽然经常饱受来自科学界或科学崇拜者的白眼(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科学史研究者是因为“搞不了科学才去搞科学史”的),但他们自己对科幻却也是从来不屑一顾的。
另一方面,在科学史研究中,传统的思路是指研究科学历史上“善而有成”的事情,所以传统科学史为我们呈现的科学发展历程,就是一个成就接着另一个成就,从一个胜利走向下一个胜利的辉煌历史。而事实上,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中,除了“善而有成”的事情,当然还有种种“善而无成”“恶而有成”以及“恶而无成”的事情,只不过那些事情在传统科学史中通常都被过滤掉了。出于传授科学知识的方便,或是出于教化的目的,过滤掉那些事情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那些事情就真的不存在了。
还有第三方面,“科学幻想”也并不仅限于写小说或拍电影,科学幻想还包括极为严肃、极为“高大上”的学术形式。例如,在今天通常的科学史上大名鼎鼎的科学家们,开普勒、马可尼、高斯、洛韦尔、弗拉马利翁……,都曾非常认真地讨论过月亮上、火星上甚至太阳上的智慧生命,设计过和这些智慧生命进行通信的种种方案。以今天的科学知识和眼光来看,这些设想、方案和讨论,不是臆想,就是谬误,如果称之为“科学幻想”,简直就像是在抬举美化它们了。然而,这些设想、方案和讨论,当年都曾以学术文本的形式发表在最严肃、最高端的科学刊物上。
穆蕴秋的博士论文,恰恰就是将天文学史上这些在今天看来毫无疑问属于“无成”的探索过程挖掘了出来,重现了出来,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这些“无成”之事后面的科学脉络和历史背景。她以惊人的勤奋和毅力,通过天文学史上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案例,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科学发展过程中,“科学幻想”和科学探索、科学研究之间的边界,从来都是开放的。或者可以说,“科学幻想”和科学探索、科学研究之间,根本不存在截然分明的边界。
所以,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科学幻想不仅可以,而且应该被视为科学活动的一部分。我们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卷2期(2012年)上联名发表了题为《科学与幻想:一种新科学史的可能性》的论文,集中阐释了这一结论及其意义。
穆蕴秋的博士论文,以及她近年与我合作的十多篇学术论文,又具有十分强烈的“示例”作用。这些论文表明:一方面,将科幻纳入科学史的研究范畴,就为科学史研究找到了一块新天地,科学史研究将可以开拓出一片新边疆;另一方面,将科学史研究中的史学方法、社会学方法引入科幻研究,又给科幻研究带来了全新的学术面貌。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这是作者为《地外文明探索研究》一书所作的序言,本报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下一版
下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