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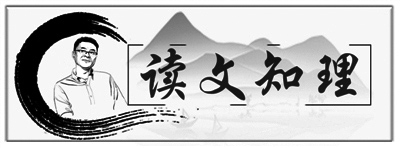 |
熟悉科学传播领域相关文献的研究人员都知道,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发布了巴德默报告,即《公众理解科学报告》,该报告提出“理解”不仅仅包括对一些科学事实的了解,还包括对科学活动及科学探索之本性的领会。显然公众理解科学已经超越了传统科普的科学知识层面,并且扩展到了科学态度等维度,也就是说要通过一系列做法弥补公众在科学态度方面的缺失,因为“科学家职业责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促进公众理解科学”。这个报告吹响了促进公众对科学理解的号角,并且为英国,甚至是世界各国建立了科学传播的新范式。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新的范式仍然是缺失模型主导下的,而且“理解”是一个有关社会对于科学状况确定性的函数,这些确定性的过程是多元的,并且常常是不完整的。科学家急于表达的“科学”,并不一定是公众理解中的“科学”。
在信息时代,特别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极大地丰富了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同时公众也开始根据自身需求主动地检索和获取信息,公民意识的觉醒呼吁对科学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这也促使科学传播转变为双向互动的模式,即公众参与科学。
2000年,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发布《科学与社会》报告,该报告认为过去的科学传播只是从科学共同体到公众的单向的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而当前的科学传播应该聚焦于对话,或者说科学家与公众的双向交流与互动。该报告的发布方敦促科研机构从单向的传播扩散模式转向各利益相关方介入的对话模式,并且对科学政策交换意见。在此模式的指导下,一系列报告开始把焦点放在了公众参与科学上,也就是说,科学大众化的模式开始从单纯的传播,走向了公众参与。
在公众参与科学模式下兴起了一系列运动和倡议,包括科学咖啡馆、愿景工作坊、协商民意测验、公民陪审团、共识会议等等。但是研究发现,这些活动的参与者不仅了解到了所关涉科学的技术层面信息,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也关注科学话题的社会、伦理、经济意义和启示。当然这种参与提升了他们参与科学决策的能力,也增强了他们参与科学和技术决策的意愿。
2017年4月,英国下议院科学和技术委员会发布了题为《科学传播与参与》的报告。该报告就认为:在科学意识和科学传播方面,公众在很多方面对科学兴趣浓厚,但是在让目前还没有参与到科学中的人参与进来方面存在着集体性的需求。另外,英国研究理事会将公众参与界定为:“促进个体和群体之间争论和互动,并且创造一种人们讨论科学议题的氛围。从决策层面上来说,它可能不会产生结果,但是它提升了人们对这些议题的兴趣和意识。科学家可以与公众进行交流,公众之间也可以彼此交流”。
应该说,公众参与科学是促进科学民主化的一种途径和方式,但是公众参与科学应该发生在哪个阶段,在多大程度上参与进来,这些都是研究者关注的问题。比如温内等人就指出这种参与不应该仅仅出现于某个产品被引入市场的时候,而应该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模式,也就是说在初始阶段就应该能考虑公众参与的可能性。《有效的科学传播:研究议程》则更进一步,认为“公众参与是了解科学信息所针对的受众的关切、问题和需求的重要方式”,因而公众参与越早越好。否则,公众参与就依然是某种缺失模型下的公共关系和拓展活动。
公众参与的益处在于理解公共舆论、价值和知识,以便与利益相关者建立更好的关系,促进公众对科学和相关机构的体制性信任,让科学政策更具活力和可信度。具体而言,公众参与可以让决策者、利益相关者与普通公众建立更好的关系,改善未来的传播,同时也可以让专家获得更多的技巧、经验和信心,丰富其研究。
同时公众对话可以促进决策者、利益相关者与公众建立更好的联系,提升科技应用的针对性,改善科学传播形态,优化科学传播效果,促进科学应用研究更加有的放矢。这“不仅是听取不同公众群体的意见,更是让决策者在公众参与的过程中保持一种民主的意识,通过参与模式让公众不断地体味到决策的系统化,从而保证科学技术的决策与其他决策一样具有重要的民主意义。”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下一版
下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