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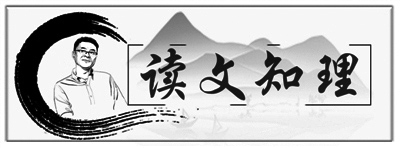 |
调查显示,公众整体上对科学和技术持积极的态度,但是涉及到具体议题,尤其是具有争议性的议题时,公众的态度就会出现极化。那么个体是如何形成对某项科学技术的看法的?科学事实在其中又发挥了什么作用?或者说个体在看法形成和决策制定的过程中,是否会单纯地依赖于科学事实?
一项新的科学技术能否在市场上取得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的接受程度(这有点类似于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传统上的观点认为,公众对科学了解的越多,他们对科学和技术的支持程度就会越高,因而赢得公众支持的方法和途径就是为他们提供尽可能多的科学知识,也就是说,让公众具有更多的科学素养。然而,其他研究则表明,个体在对新兴科学技术几乎不了解,或者说不具备相应知识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形成自己的看法,同时他们对新兴科学技术的态度取决于有关科学的事实性信息之外的一系列其他因素,比如价值观、对科学的信任、框架、既有知识等等。
为了搞清楚公众在对新兴科学技术形成态度和观点时,都有哪些因素发挥了作用,框架研究的大师德拉克曼(James N. Druckman)和博尔森(Toby Bolsen)以碳纳米管和转基因食品为例,探讨了框架、动机性推理与有关新兴技术的观点之间的关系,并将研究结果于2011年发表在了《传播学期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上。该研究生动地展示了动机性推理和确认偏见如何影响人们对新兴科技的态度(有关框架的问题,我们会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详细介绍),这对于我们如何开展好科学传播具有一定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科学传播从业者和科研人员希望公众可以根据他们获取到的全部信息和知识来理解或评估某项科学技术,但是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当面对新的不熟悉的科学技术时,人们会利用一系列心理捷径来减少心智方面的努力,以对科学证据信息评估。因为研究显示,人类在心智努力上是一种天生懒惰的物种,这在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的畅销书《思考,快与慢》有类似的论述。比如人类会在不同场合调用两种不同的系统(“系统1”和“系统2”)来做判断。而动机性推理则是“系统1”的一个属性或者说特征,在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出版的《有效的科学传播:研究议程》中,将动机性推理界定为,“对深植于大脑信息处理机制的基本结构中的那些能即刻获得的信念和感觉予以支持的一种判断的系统性偏见。”也就是说,大多数公众在接受与他们的立场相矛盾的事实、证据和论点时,他们会产生一种天然的抵触情绪。
德拉克曼和博尔森的研究表明,在制定决策的各个阶段,事实性信息对观点的形成虽然具有影响,但是这种影响非常具有局限性,也就是说,在形成对科学技术的态度方面,仅仅提供事实性知识是不够的。同时一旦人们形成了某些看法和观念,那么扭转这种先入为主的看法就非常困难,因为人们会用有偏见的方式来处理新出现的事实性信息。也就是说,如果新出现的信息与他们的既有理念相一致,那么他们会比较容易地接受。但是如果这些信息与他们的价值观、立场等相冲突,那么他们有可能会去努力地同化这些信息,如果同化失败,则可能会对其摒弃,或者置之不理。
随着对科学传播本身的研究的深入,以及对心理学和传播学等领域的理论的借用,越来越多的科学传播研究人员意识到了这些新的洞见对科学传播实践的启发,同时也试图从理论上构建出更加有效的模式,从而更好地指导科学传播工作。比如近年来日益获得关注的“科学传播的科学”(美国科学院曾举办了几次有关这个主题的研讨会)从不同领域对科学传播进行了研究和考察,也引入了其他学科和领域的一些理论框架,致力于把科学传播作为一种科学来考察,以及用科学的方法来推动科学传播的研究与实践。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下一版
下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