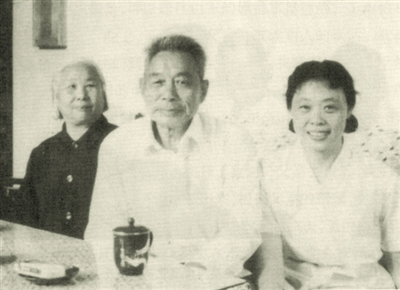 |
| 束星北(中)夫妇和女儿束美新合影 |
科海钩沉
今年4月,在一次纪念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叶企孙冥诞120周年的活动上,早年受叶先生亲炙的物理学史家戴念祖谈到一件令人反感的事。他大意是说,这些年谈叶先生的书和文章多了,是好事,但有一种现象要不得,就是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比如说文革期间叶先生沦落到在街头流浪要饭,完全是子虚乌有。如果任凭这种随意杜撰、添油加醋的写作泛滥,对严肃的科学史研究以及面向公众的科普教育,都是一种严重戕害。笔者不禁回想起十几年前一部引发学界众多质疑的科学家传记《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以下简称《束档》)。
严格说,《束档》并非一本学术传记,而是一部传记文学,但传记文学几个基本特征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人物和事件的真实性,其余的文学性、艺术性等均是在此基础上的发挥与再创作。可该书的封底这样写道:他被誉为“天下第一才子”;他的理论物理修养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内难有比肩者;他的教育才华也无人可以企及。当年国内几位科学史家实在坐不住了,他们认为,不能胡乱地给历史人物贴金。按照发文的时间顺序,对该书提出强烈质疑的三位科学史家分别是樊洪业、许良英和关洪。樊是近现代科学史家,许和关是物理学史家。三位专家均严重质疑该书提到的束星北与爱因斯坦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许良英早在1993年就提出过。
原来,1993年是束星北逝世10周年,其故乡江苏邗江专门编印了一本《物理学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的小册子,其中收录有许良英写的《忆束星北先生》。这本册子的附录同时收录有许良英质疑束星北曾担任爱因斯坦助手一说的一封信,主要质疑的是1979年束星北署名(其实是口述,记者采访)发表在《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同时在附录中收录了核物理学家李寿枬为束星北辩护的一篇文章。可见,在《束档》出版之前,事件真伪至少存有争议。尽管《束档》有意回避了束星北是否担任过爱因斯坦助手这一问题,但就两者的交往,仍采用了束星北口述文章的说法,倾向性很明显。
其实在《束档》出版之前,有关束星北是否担任过爱因斯坦助手的问题已经有了定论。1997年,许良英收到科学史学者胡大年在查阅爱因斯坦档案时发现的一封信,是1943年束星北在湄潭寄给爱因斯坦的信件,信开头的第一句便是:很遗憾我无缘与您相识,但从我孩童时代到如今研究自然科学,您在自然哲学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一直激励着我(笔者译)。束星北声称在爱因斯坦身边的日子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如果事情属实的话,1943年这封信开头的话就显得有些匪夷所思了。如今,爱因斯坦的档案已全部在线公开,这件档案随时被人可以查阅、核实。任何人在这一问题上如果再为束辩护,都显得苍白无力。
关洪则直接指出,《束档》是一部浮夸的科学家传记,特别提到为了拔高束星北,在一次本是普通的学术交流中,采取了丑化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专家王竹溪的手法,以“美化”束星北。类似的例子还有,谈物理成就,说他不亚于王淦昌;说数学素养,称他不逊色于苏步青。此外,胡乱地为传主戴高帽,诸如“中国现代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那个时代的中国物理学大师”云云。学界为此集体愤怒,自在情理之中。
科学家传记,即便是传记文学,也应秉笔直书,何况对束星北这样一位深深打上历史烙印、卷入历史洪流的物理学家,其命运与历史交织的真实故事足以令人扼腕、打动人心,而不需要任何矫饰与装扮,更不能为了造神把同时代的历史人物踩在脚下。
值得称道的是,像樊洪业、许良英和关洪这样的科学史家(特别是许良英,本身还是束星北的学生),秉持“求真”的科学精神,表现了他们敢于批评、勇于担当的可贵品质。弘扬科学精神,必须牢牢把握其最本质的“求真”精神:挖掘科学故事,不容青史尽成灰;书写科学人物,青史何须镀金辉。








